每年五月十五,我总要穿过三十里油菜花田去给爷爷上坟,裤脚沾满蒲公英绒毛的时节,每片草叶悄悄攒着晨露,如同祖父腰带铜扣上永远擦不亮的绿锈,坟地边缘歪斜生长的半裸松树托着两只灰喜鹊窝,杂草深处埋葬着我亲手扎的枯枝秋千,铁链条早已和牵牛花藤绞缠成碧绿的锁链。
春泥
通往坟地的黄泥小路会被清明雨水泡得酥软,踩下去吸吮鞋底的力度像极爷爷临终前攥我的手,留守祖宅的最后那只狸花猫总蜷在碑石凹陷处,用尾巴抹去碑文上"甲午年生"的苔痕,我在褪色红漆描金的供龛前摆上枣泥饽饽,氤氲的热气里隐约重现爷爷裹着老羊皮袄坐在灶台前的身影,他总把第一锅蒸好的窝头掰成两半,在我手心里藏进一颗腌梅子。
蜻蜓点破水面时,会发现坟包西侧的小水洼盛着整个破碎的穹苍,去年盘旋的凤尾蝶停在新发竹笋上,翅尖鳞粉滚落处,嫩绿茎秆倒映着民国三十年爷爷牵着骡车跋涉在沦陷区的模样。"我在德州城门洞里见过十六架轰炸机编队,翅膀上的红膏药比秋天染坊晾晒的茜纱还要刺眼。"当童年听过的故事随纸钱灰飘向天空,成串的泪珠便坠落脚边的雏菊丛。
夏天的蝉蜕
蝉蜕壳叮在青石碑顶的第廿三年盛夏,这里已经是睡着一百四十七位先人的家族墓地,母亲总在天蒙蒙亮时挑着扁担来添供果,父亲沉默地劈开疯长的野蒿,镰刀擦过青石的火星惊走了瞪着琥珀眼睛的黄鼠狼,我在老松斑驳的树皮下发现1998年刻下的身高刻度,那年祖父还能单手把我举上枝头摘榆钱。

一群白鹡鸰掠过头顶时,风里忽然飘来隔世的笑骂:"傻丫头,蝉蜕要留着入药,治你夜里盗汗的毛病。"麻酥酥的触感和三十五年前别无二致——爷爷枯瘦的手指轻轻弹我耳垂,当时老宅西厢房的药吊子夜夜蒸腾着忍冬藤的苦涩,而现在蓝印花布裹着的蝉蜕还藏在我首饰盒底层,与祖母陪嫁的银镯互为封印。
秋天的陀螺
暮色染红柿子的时候,荒草间旋转的野蔷薇种子总让我产生错觉,那年爷爷用降龙木削的陀螺仍在坟前土坑里打转,沾满蛛丝的木纹裂痕间渗出松香,被霜打蔫的蒲公英像是未烧尽的黄表纸,风起时漫天雪籽般的绒毛里,飘着父亲从爷爷马靴里翻出的民国三十七年粮票。
"把手抬高,看我给你劈个阎王爷的惊堂木。"梧桐叶纷飞中浮现老人挥斧劈柴的身姿,削薄的木片顺着抛物线钻进我的羊角辫,而今斜插在供盘里的艾草渐渐褪成灰白色,只有爷爷手雕的那个滚铁环小人仍旧咧着参差的豁牙,守着往生界碑石缝里开出的蓝紫色桔梗花。
冬天的马蹄铁
初雪覆盖坟堆第一个清晨,马蹄铁的轮廓会在冻土下显现幽蓝的光,父亲教我用枯枝扫开积雪的动作,和当年爷爷示范锄地的架势一模一样,供桌石缝里嵌着的半枚光绪通宝突然松动,掉在我掌心时腾起一小团白雾,恍惚见爷爷把浑圆的银元按在算命瞎子手里:"给这丫头批个流年"。
烧化的锡箔灰被北风卷向黑松林深处,忽明忽灭的红光里我看见十二岁的自己跪在草席上,孝帕垂落的阴影里停着只碧玉般的纺织娘,而今那个哭灵时偷吃祭品糯米糕的小丫头,已学会用凤仙花汁把指甲染成祖父寿衣的颜色。
在永恒的门槛上
上元节最后一盏河灯漂远时,泥土下的马蹄铁开始敲打岁月的岩层,送丧唢呐声与喜轿铜铃声在时空褶皱里共振,祖父坟头上野蛮生长的山茱萸仿佛是新娘鬓角的绒花,我摩挲着碑座日晷般的凹痕,突然读懂老宅门楣上祖父用金漆描的《维摩诘经》——"若见生死即是涅槃"。
百年柿子树根始终紧紧搂着青石墓碑,如同爷爷临终枯爪扣住我的指节,当渴睡的山雀把羽毛藏进碑面裂纹,我终于明白人间的露水总在天亮前消失,但有朵波斯菊永远开在1932年盛夏——刚中举人的祖父策马驰过青纱帐,马蹄惊飞的蓝蝴蝶落在他斜插宫花的新冠缨上。
日头偏西时我把三炷香插进铜炉,忽然发现藏在裤袋里的核桃竟发了芽,三十五年前祖父种在我手心的那棵,此刻正在石碑后与荒草纠缠成碧色的网,枯枝秋千的牵牛花藤突然绽放出淡紫的火焰,风里传来竹哨声般的呜咽,某个瞬间,我确信看见祖父解下酒葫芦倚在松树下,酒香漫过整个黄昏的坟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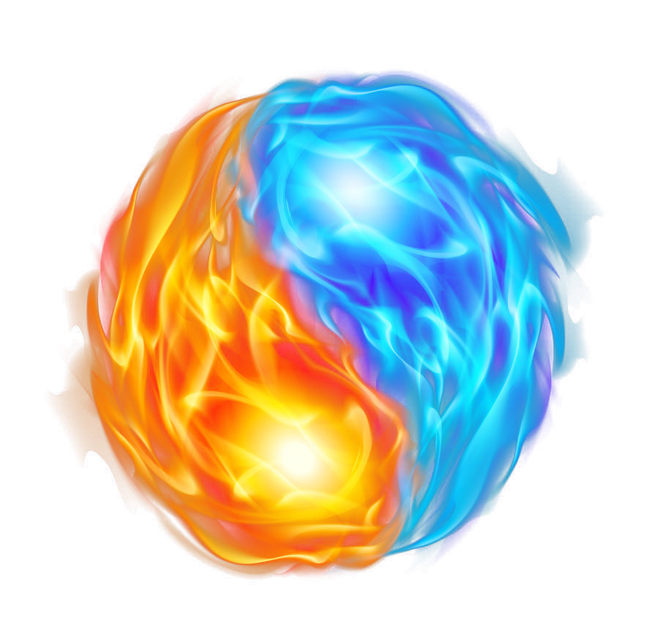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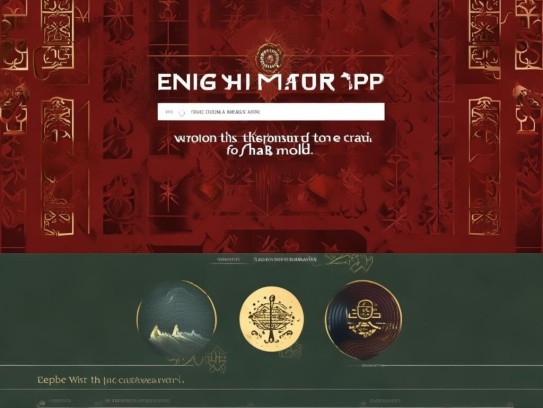
发布评论
发表评论: